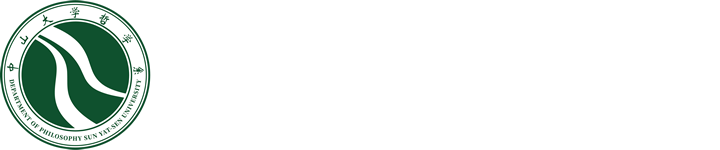“哲学前沿”课程讲座第十讲纪要 | 陈少明:什么是存在——再论《兰亭序》的经典化
2024年5月10日晚,太阳集团城娱87222023级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十讲在锡昌堂103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太阳集团城娱8722陈少明教授主讲“什么是存在——再论《兰亭序》的经典化”,太阳集团城娱8722吴重庆教授主持讲座。

吴重庆教授介绍了陈少明教授的研究情况,言及其对太阳集团tcy8722乃至中国哲学学界的显见影响,重磅推荐大家去阅读《做中国哲学》、《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这两本书。
陈老师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开启了今晚的讲座。他说,哲学没有固定的对象,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研究,之所以选择《兰亭序》,是因为这件书法作品独特的产生、发展、经典化过程,揭示了一种动态的存在方式。这一“存在”不同于西方哲学家所讲的形而上学的名词性的“存在”概念,而是动词性概念。
陈老师论述一般的“存在”的三种样态:其一是物理的、三度空间中的人、事、物;其二是意识的,存在于人脑中的问题、现象;其三是文化或信息的,它脱离意识,借助文字等物理载体传播。这三种存在状态不同,但其反面均是“不存在”,就这个意义上,陈老师将它们整合起来,探讨“存在”。《兰亭序》同样具有存在三样态,分别是当时的兰亭集会活动、人们关于活动的意识与想象、记录在文字中的兰亭文,三样态可相互转化:事件进入意识,并由文字记录,而后人又可以借助文字,使隐没的事物进入意识,甚至复刻出与原物品相类似的三度空间的物品存在。《兰亭序》便经历了这样一个诞生、隐没、再生、经典化的过程。
一 诞生
《兰亭序》这部书法作品的诞生是事件与作品的复合。
事件发生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一群名士聚于兰亭,饮酒赛诗,当时“惠风和畅”,在座者“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王羲之感怀美景佳事,为之作《兰亭序》,记录“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盛况,抒发“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之逸情。
赛诗活动结束,兰亭文和兰亭帖随之面世。兰亭文首先是存在于意识、可诵于口、传于耳的文章佳句,不经过文字、纸张也能相互传播,当它被文字记录、在纸上留痕后,就以书法作品的物质形式,存在于三度空间中。这里涉及文和字的区别与联系。
陈老师分析道,文是由字组成的;字可借言传达,故文也体现在言中。文的早期传播形式是口耳相传,比如诗的起源就来自人们的口头吟诵、传唱,这说明文不一定要在特定载体上读到,听闻亦可。
但字有两重意义,其一是语言意义,通过阅读识字可以获得其背后的语义,不论字的字体或笔迹如何,只要立意好就是好文章。其二是书法意义,将字书写成形后,会关注其审美形象,书法的创作或鉴赏都是通过视觉图像来完成的。
所以,兰亭文与兰亭帖对应着不同的存在形态,在后来也面临着不同的传播命运。
二 隐没
兰亭帖被写成后,从永和九年(353年)集会,到至武德四年(621年),共264年间,原作基本下落不明,陈老师用“快闪”来形容这种面世后迅速隐没的现象。
一种说法是,王羲之珍爱此帖,特将其流传给子孙后代,至第七代孙智永,后出家,名永禅师。禅师精通书法,据说写烂的笔头可装满满五大竹筐,百年归去后,由其弟子辩才继承《兰亭序》,他亦是书法爱好者,曾将《兰亭序》藏在所居方丈室的房梁上,轻易不示人。另一种说法是,《兰亭序》在南梁国乱后流落在外,于陈朝天嘉年间中期,一名僧人得到,后来献给陈朝宣帝,陈被隋灭,《兰亭序》则落入隋晋王杨广之手,但不受王重视,有僧人相借后不曾还回。至唐朝,秦王李世民多方求取,终于武德四年将《兰亭序》纳入王府。
在被李世民找到之前,《兰亭序》作为三度空间中的存在物,因少为人知,在世人中没有“存在感”。但是,兰亭帖虽是隐没的,却不妨碍兰亭文的传播。文可以间接传达帖曾经存在的消息,例如后人在阅读相关兰亭文章后,可以对当时“曲水流觞”的情景加以想象;可以由所见的文推想其背后必然存在一个文字形式的字帖。正是一直在传播、存在的文,为帖的重新出场做了铺垫。
三 再生
唐太宗得兰亭帖的故事,颇具戏剧性。据何延之《兰亭记》所述,太宗听政之余,常常临写一些《兰亭序》的临摹品,但四处求购原作而不得。听闻永欣寺主持辩才密藏兰亭帖,见猎心喜。于是派御史萧翼,乔装成书生,与辩才多方周旋骗取信任,最终以《职贡图》作诱饵,成功骗抢。
太宗得到兰亭帖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曾亲自在《晋书王羲之传》中为《兰亭序》写评语:“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幡,势如斜而反直。”《兰亭记》中还记载了太宗临终前,对兰亭帖含泪不舍,于是向高宗讨要,并嘱之以帖陪葬的故事。自此以后,兰亭帖常埋地下,可以说进入了物理意义上的存亡,但它仍有“存在感”。
四 经典化
书法作品需要形的鉴赏,眼观手触才能传承,如果只有孤本的话,那必然无缘于传播、深远传承。陈老师指出,《兰亭序》之所以成为经典,得益于临摹。太宗曾命近臣赵模、冯承素等各拓数本,他自己则“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同时,束世南、欧阳询等名家权臣均奉敕临帖。
在此,有临有摹。陈老师剖析了摹与临的区别,摹是把薄纸覆在古帖上摹写,要求复制的结果准确无偏差;而临则是将原作的笔法内化,是一个追慕原作者精神的心理体验过程,临品会带上原作者与临者的双重印记。
陈老师接着说,虽然临摹壮大了《兰亭序》的声势,但毕竟影响力只在朝臣,其经典化的标志其实是石碑定武兰亭。碑由唐明皇下令刻立,比纸本更耐用、持久,作为一种永久模板供人拓取,虽然石碑后来遗失,但其代身传遍天下,“定武儿孙遍天下”(王文治),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后来,从帝王到名家,宋有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元有赵孟頫,明有文征明、董其昌等,都临摹、拓写过《兰亭序》,这些临摹品与相关的传说、序跋汇合,构成一种经典化的传统。
传统由行动塑造:诸多相似的单数或少数人的独立行动,组合起来变成多数人的运动,运动一旦形成且反复起作用,就进一步造成传统。传统的存在,不是某一文物的遗存,而是文化的形成。
五 遗产
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经过宋唐、民间与官家的多次转手,早已不知所终,但却留下了一套衍生品的谱系:临写、摹拓、石刻、木刻、影印、数码复制、赝品。摹不如临,机械的复制又不如手工的摹拓,赝品更次,它在伦理上构成对艺术原创性的伤害以及对原作者的冒犯。
《兰亭序》不同于故宫、长城这样的物质遗产,也不同于道德仁义这样的精神遗产,它是一种程式、方法,可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式微,但没有失传的危机。书法的遗产意义如同汉语一样,必须在整个民族文化中定位。
讲座至此接近尾声,陈老师进一步引申道,《兰亭序》的经典化过程体现了“存在”的不同现象与特征,即“存在三态”的相互转换与作用。而这种历史沉浮中的“存在”,显而易见并非名词,而是动词,与其说在讨论“什么是存在?”不如说在讨论“事物是如何存在?”《兰亭序》是器,但是相对于道的器,它的经典化不是物理事件在自然力量下发生的演变,而是与人的意识、行为相关,应此要放在整个人类文化视域中加以探讨。
互动交流环节
吴重庆老师随后进行了精炼总结,他认为这也是一场“文的传统如何创发、延续”的讲座。这个“文”是“文以载道”的“文”,也是“文质”的“文”,文既可以用来载道,也可以标榜文人雅士群体自身的身份。文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
同学们对讲座兴味未尽,踊跃提问。针对“文在艺术的经典化过程中是否一定必要”,陈老师解答道,对广义的艺术而言,语言、文字是重要载体,但有部分对象是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述的,因此语言对艺术不是必要条件。
针对“中西方经典的形成的异同”,陈老师认为,中西方经典的形成特征有同有异,一个重要的共同处在于经典是被解释而非创作出来的,一些在传播中被认为有精神价值的文本被人反复不断引用、解释,才尊为经典。
针对“想象力在哲学中的应用”的问题,陈老师指出,想象力是人面对过去、未来必须有的素质,而不限于哲学;哲学要求的想象力的独特性在于,它必须把想象变成有逻辑、有结论的一个结构。
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