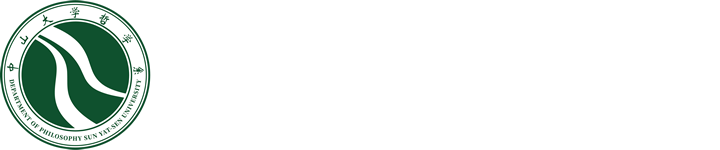书讯 | 张铜小琳《儿童“开—端”与教育之道》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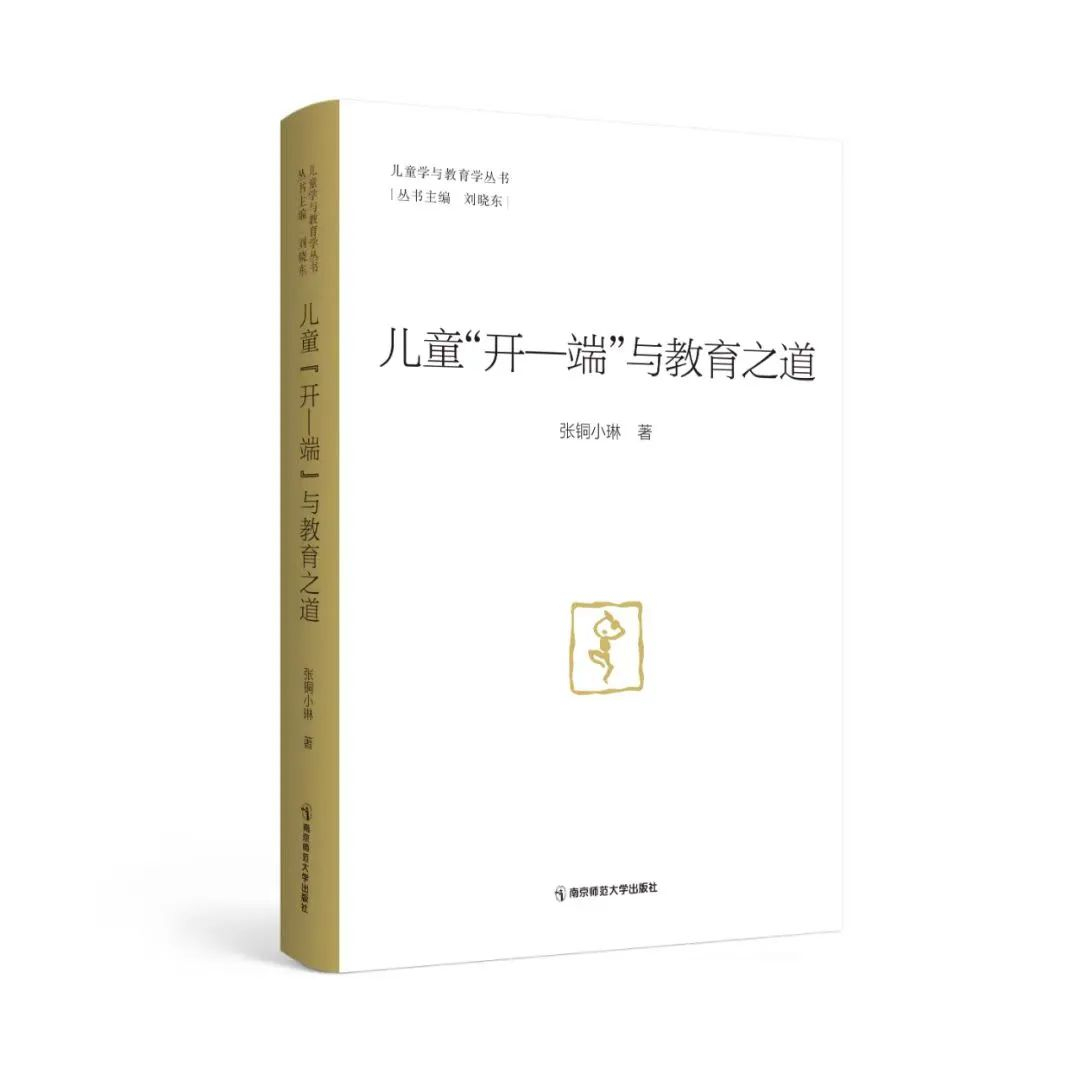
儿童学与教育学丛书
儿童“开—端”与教育之道
张铜小琳 著
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ISBN:978-7-5651-5739-4
作者简介
张铜小琳,安徽芜湖人。教育学博士,太阳集团城娱8722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童年哲学、教育哲学、游戏哲学。迄今已在《基础教育》《教师教育研究》《上海教育科研》《新儿童研究》《哲学教育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本书以“开—端”概念阐释儿童在人生中的地位与存在方式,揭示从儿童而来,由儿童开显,向儿童复返的“成—人”实质与过程,呼应“开—端”性童年的历史回响,并发送时代呼告:儿童“开—端”是儿童和成人内在统一(同一)与外显差异的原型,是人类世代生存的始基与根据,它在游戏中显现,在教育中实现,亦由此道出教育的“根”“本”——回到儿童自身。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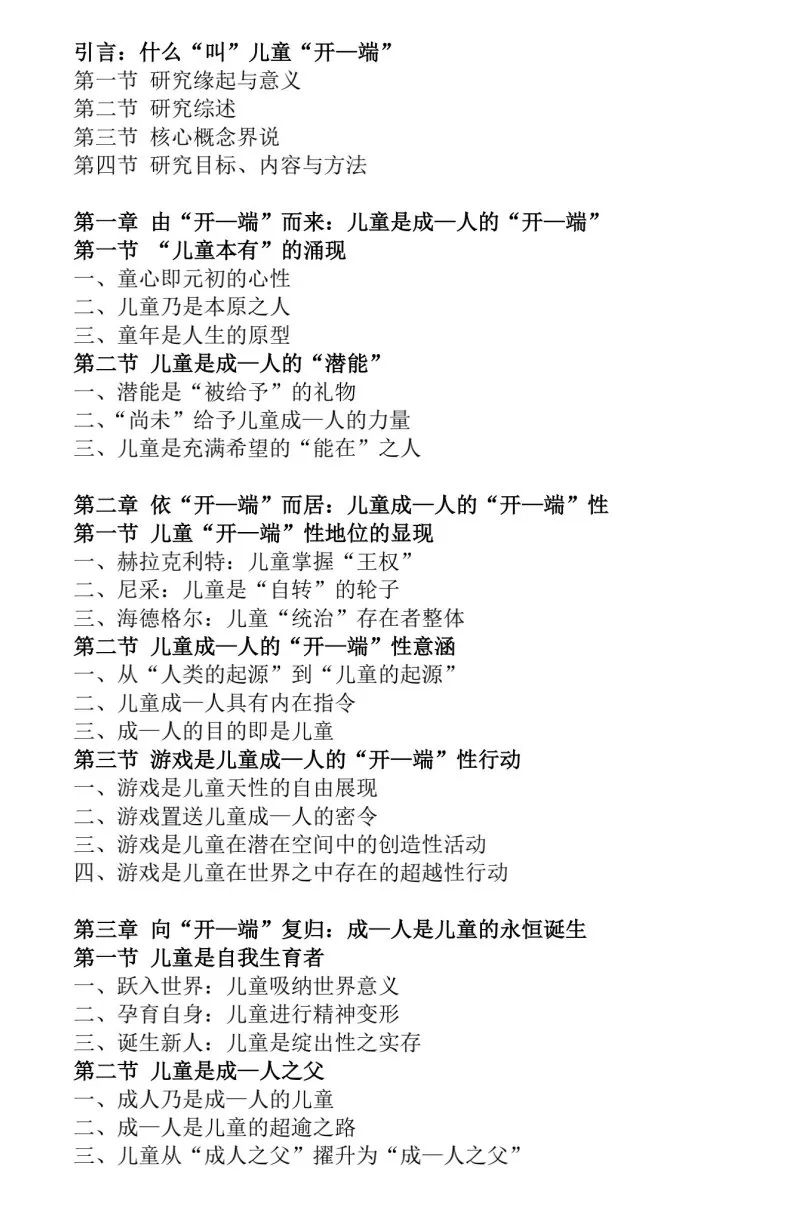
前言
人们通常对“开端”持有端点式、单向度、流逝性的固化理解,这也导致了对儿童的误解与漠视。本书通过对“开端”概念的历史溯源, 融通多学科领域对 “开端”内涵的多重发现,进而提出以“开—端”来认识、澄清、剖析与显现事物的本质之源, 恢复“开—端”所原有的“开始”与“统治”相统一的意涵,从而揭示“ 开—端”是起源、根据、目的的统合,具有去两极化、永恒复返的生生之意。儿童作为人之存在的“开—端”,显现出成—人的“开—端”性,也体现了儿童“开—端”的思想。所以,对“开—端”的本真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儿童,还原儿童的本真样态。
从“开—端”本身来看,它是事物的本质之“根”、生成之“源”以及发展之“果”。因此,儿童“开—端”也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 儿童是成—人的 “开—端”。作为元初心性的童心、本原之人的儿童以及人生原型的童年均是儿童本有的涌现。这亦源自儿童是成—人的潜能,潜能作为“被给予”的礼物,既体现于儿童拥有成—人的力量,也表现为儿童是“能在”之人。第二,儿童成—人具有“开—端”性。因为儿童具有“开—端”性的地位,并且,儿童是成—人的起源、内在指令和目的。游戏作为儿童的天性,它是儿童成—人的“开—端”性行动,因而具有存在论的根据与意义。第三,成—人乃是儿童的永恒诞生。儿童作为跃入意义世界中的精神胚胎,通过“吸纳—变形—绽出”生育自我,而诞生为 “新人”, 这种“诞生”在“开—端”的永恒复返中成为不断地“重生”。由此, 成—人也是儿童对自身的超逾与创造,儿童与成人的紧张对立关系在成—人中获得消解与解放。据此,儿童从“ 成人”之父擢升为“成—人”之父。
儿童“开—端”性地成—人也澄清了童年的“开—端”性。传统以时间性为基础的童年观会疏离人的存在,从而陷入了童年消逝的困境,形成童年是被社会文化所建构的浅见,也因此将“社会化”作为儿童成—人的主要目标。但随着时间性童年观的演进,“时间”与“存在”走向了统一,它呼唤着一种关切儿童存在的童年观的诞生,这便是“开—端”性童年。因为童年就是儿童的“开—端”性, 也即“儿童性”。“开—端”性童年才是本真的童年,回到童年的本源,呼告童年从“儿童的时间”转变为 “时间中的儿童”。于是,儿童的存在从时间的洪流中跃出,进而发现“开—端”性童年蕴含着内在性、力量性、丰富性、永恒性与根基性的特性。
教育作为人类的原初存在现象,它的本质与本旨就是育人与成—人。所以,教育之道与儿童“开—端”具有本质关联:一方面,儿童“开—端”乃是教育之道体;另一方面,儿童经由教育之道路而“开—端”。因为,儿童本有与潜能为教育开出了道路,儿童的内在发展也为教育之道树立了路标。因此,教育应当去除成人对儿童的“前见”与“预设”,才能还原与发现学习的本质,也就是要回到儿童自身。在这种本真的教育中,儿童能够以“做儿童”来创作自身,并通过教育来创造世界,让教育真正成为儿童成—人的艺术。
儿童学与教育学丛书 总序
刘晓东
辩证地看,教育学即儿童学。何以见得?
卢梭认为“人的教育”“事物的教育”应当与“自然的教育”保持一致,而“自然的教育”其实就是指儿童自身所体现的统领儿童成长的自然倾向、自然目的、自然意志、自然规律,是儿童的自性,是赤子、童心。教育应当与“自然的教育” 保持一致,其实质就是教育应当“跟从儿童”。大致说来,这是整本《爱弥儿》洋洋洒洒所讲论的核心思想。
也正因为如此,卢梭《爱弥儿》所实现的“对儿童的发现”,才会具有如此伟大的历史意义。而正因为卢梭有了“对儿童的发现”,卢梭的教育学才成为名副其实的“跟从儿童”的教育学。
我们研究儿童,探索儿童成长的规律,探索教育规律,这本身就是为了“跟从儿童”,并且这本身就是“跟从儿童”。无论是自在地、合目的合规律地展开教育自身,还是自觉地按照儿童内在发展的规律而开展教育工作,教育的现实形态都必然体现为“跟从儿童”。
其实,西方现代教育学在中国的儒道释各家中均可找到可以相互对接的理论根基, 例如《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就可视为现代教育学的内容提要,而这三句话的的核心在于“率性”二字。率性,即遵循天性。尊/遵天命、寻/循天性,其实就是现代教育学的基本纲领。怎么把握人所承载的天命天性, 则依赖于儿童研究。有对儿童的发现, 必然导致对现代教育的发现。
我个人多次讲,儿童研究至少是教育研究的一半。我的说法偏于保守。之所以保守,是因为我自己从事大量儿童研究,我担心别人说我出于私人利益而过分强调儿童研究的重要意义。(尽管我投入大量时间从事儿童研究,但儿童研究却是学术公器,是公共资源,是公共事业。) 后来, 我看到杭州师范大学张华教授断言 “教育学即儿童学”,我是完全赞同的。
从夸美纽斯的“师法自然”的教育学,到卢梭的自然教育论,再到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再到杜威的学科知识的逻辑应当符合儿童心理的逻辑,等等,这类教育哲学和课程哲学的实质是“教育应当儿童化”“课程应当儿童化”。现代教育(学)所追求的,就是让儿童成为教育的“红太阳”。“儿童”这颗教育(学)的红太阳冉冉升起的过程,即是现代教育学持续推进的过程。
尽管教育学也要研究知识、道德、审美、技能等等文化世界的东西,但是这些文化世界的东西一旦进入课程,就必须建立于儿童研究之上,必须转换为儿童身心世界的东西,才能保证教育的成功——既符合儿童的自然成长和内在发展、 儿童的兴趣与需要,又能在教育过程中实现外部文化的生动地复活乃至提升。也就是说,全盘考虑之下,教育学是一刻也离不开儿童研究的;也就是说,“教育学即儿童学”的说法是正确的。
“教育学即儿童学”,体现着教育学与儿童学的辩证关系。
2022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