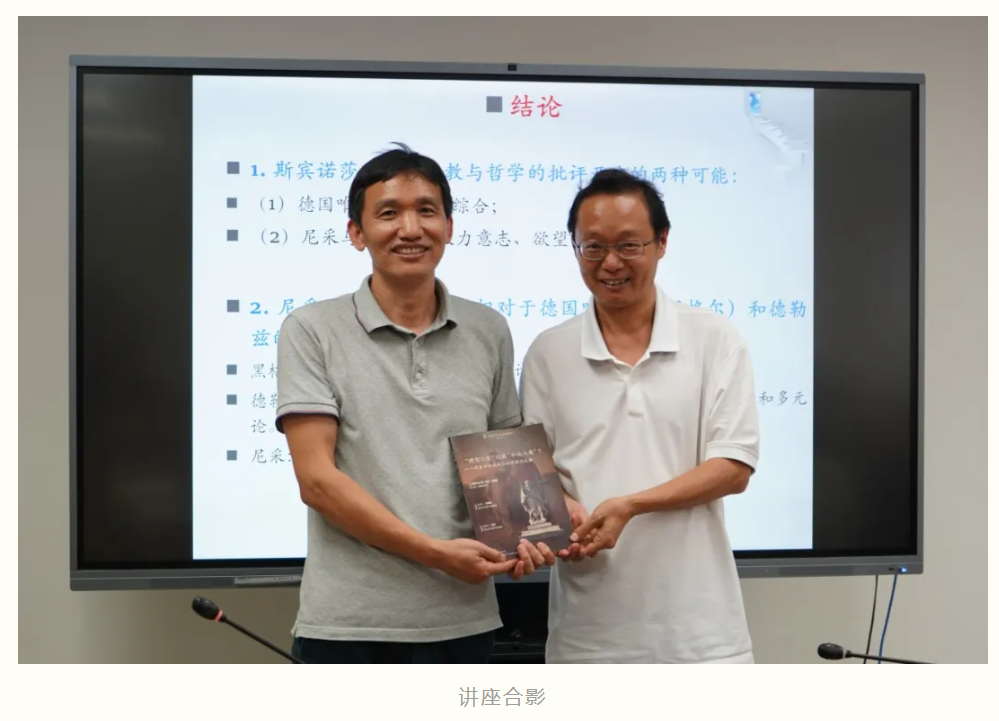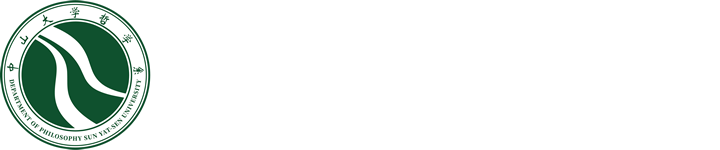“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讲坛”第二十一讲纪要 | 吴增定:“理智之爱”还是“命运之爱”?——尼采对斯宾诺莎的理解或误解
2024年4月13日下午,“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讲坛”第21讲在锡昌堂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吴增定教授,他的报告题目是“‘理智之爱’还是‘命运之爱’?——尼采对斯宾诺莎的理解或误解”,本次讲座的主持人为朱刚教授。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朱刚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吴增定老师,并对同学们的热情表示感谢。吴增定老师表示,中大太阳集团城娱8722的学术氛围始终让他感到亲切。讲座在愉悦的氛围中开始。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吴增定老师首先给我们呈现了斯宾诺莎的双重形象。他介绍了哲学史上对斯宾诺莎哲学的两种不同解释。一为德国唯心论的视角,一为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的视角。前者强调了斯宾诺莎哲学中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一面,代表人物为谢林、黑格尔以及费希特。在18世纪德国哲学界泛神论之争的背景下,他们挖掘出了默默无闻的斯宾诺莎,赞赏他提出对整个世界的一元论解释。但他们也认为,斯宾诺莎哲学的贡献仅此而已,其缺陷在于缺乏主体性、自由与能动性,局限于因果必然性乃至宿命论。在黑格尔看来,专注于静止僵化实体的斯宾诺莎哲学并非传统理解的无神论哲学,而是一种“无世界论”哲学。自此,德国唯心论将斯宾诺莎的哲学解释固定下来。
直至20世纪后半叶,以德勒兹和阿尔都塞学派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提供出斯宾诺莎哲学解释的另一面向。在20世纪,法国哲学家所关心的要务之一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他们从哲学史上寻找到的、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人物,是斯宾诺莎。由此,法国哲学的斯宾诺莎研究既反对了黑格尔哲学,也反对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论所塑造的斯宾诺莎形象。具体来说,德勒兹认为,斯宾诺莎哲学并非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而是一种动力学,是关于纯粹内在性与力量的哲学。他提出“存在的单义性”来解释斯宾诺莎哲学,这是说存在即力量,存在是力量的无限表现。这颠覆了德国唯心论创立的斯宾诺莎形象;以内格里与马舍雷为代表的阿尔都塞学派则强调了斯宾诺莎哲学中彻底唯物主义、多元主义的一面,同时关注了他在《神学政治论》中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吴增定老师看来,这两种不同解释恰好契合了斯宾诺莎哲学的双重面向。首先是自然主义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强调自然的同质性原则,认为所有自然物在存在论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力量。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为追求力量而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自我保存的欲求或努力(conatus)构成一切事物的现实本质。从conatus原则出发,斯宾诺莎否定了人的优越性,并进一步批判了目的论。在他看来自然世界是同质的;其次是理性主义的一面。在此,斯宾诺莎强调因果性原则或充足理由原则。对他来说,神即自然,是唯一的实体。一切存在者的存在皆需要原因,包括神。但神的原因在自身之内,是作为内因的原因。而人能够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获得对神的认识,实现自身的自由,此即“对神的理智之爱”。这里隐含了一种理性的目的论。
由此观之,法国哲学主要强调了斯宾诺莎哲学中的动力学的面向,而德国唯心论则更强调它理性主义的一面。
在吴增定老师看来,尼采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更为客观的解释。尼采一方面肯定了斯宾诺莎哲学的内在性原则,肯定了它反对超越性、反对目的论与超善恶的一面;此外,尼采认为,斯宾诺莎发现了对力量的欲求(conatus)是唯一的实在,这与自己的权力意志学说相似。另一方面,他也批评了斯宾诺莎哲学的不彻底性,不满于斯宾诺莎只把万物理解为自我保存,而非权力意志或自我克服。同时,他也批评了斯宾诺莎对因果性原则或充足理由原则的迷信。尼采认为,它们并非自明之理,而是来自人的构造。
值得一提的是,德勒兹的斯宾诺莎解释思路便来自尼采。但他突出了斯宾诺莎哲学中自然主义、动力学的一面,弱化了他的思路中理性主义的一面,并尽可能把后者还原为前者。吴增定老师认为,在尼采哲学启发下的德勒兹解释并不如尼采本人的解释客观。
接着,吴增定老师转向了讲座的第二部分,即尼采对斯宾诺莎哲学的了解与态度变化。首先是学界有所争议的一个问题,尼采以什么途径了解斯宾诺莎哲学,又了解到什么程度。在这个问题上,绝大部分专家认为,尼采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并非通过一手途径,也即并非通过阅读斯宾诺莎原著。1881年,尼采精读了费舍尔《近代哲学史》中的斯宾诺莎章节,深受影响。这是说,尼采是根据二手研究获得了对斯宾诺莎的了解。然而,他的理解仍然是准确的。其次,尼采著作呈现出对斯宾诺莎的态度变化。在1881年前后,他采取一种高度肯定的态度,在笔记中,将斯宾诺莎与柏拉图、帕斯卡尔和歌德等人一并引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和同道,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他称斯宾诺莎是自己真正的知音。这符合我们对尼采与斯宾诺莎关系的一般理解。然而,在事实上,尼采对斯宾诺莎的肯定非常少,他在绝大多数对斯宾诺莎的提及中都批评了他。在1882年,《快乐的科学》呈现了大量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批判,首先批判了他的理智主义,其次批判了他的conatus学说是一种潜在目的论。自1885年起,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发表后,尼采对斯宾诺莎的批判更加激烈。首先,他批评斯宾诺莎的生命保存原则是一种生命的“颓废”;其次,他批评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之爱”否定了生命;最后,他认为斯宾诺莎对理性、逻辑与因果法则的肯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迷信。显然,斯宾诺莎并非尼采的真正知音。
接下来,吴增定老师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澄清了斯宾诺莎的思想谱系。首先是斯宾诺莎所体现的对神的理智之爱。吴增定老师先从尼采的理解来切入。尼采在什么意义上欣赏斯宾诺莎?第一,尼采肯定斯宾诺莎把知识看作激情,而非不动心的沉思;第二,他赞赏斯宾诺莎对传统启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中世纪哲学的否定,他们二人同样反对传统宗教与哲学中自由意志、目的论,超验的道德秩序。尽管有这些肯定,我们仍要看到二人的差异是实质性的。
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吴增定老师首先介绍了他的哲学所批评的对象:在古代,他批评了传统的启示宗教带来的超越性和创世学说,这是说,神创造世界并且保持对世界的超越;他也批评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目的论,这是说一切自然万物皆有内在目的,并非趋向目的而存在;他同样对阿奎那与迈蒙尼德的经院哲学感到不满,他们进行了融合,认为神为人的缘故创造自然,人因其灵魂的自由意志成为自然的中心。在现代,斯宾诺莎批评了笛卡尔的学说。他首先注意到笛卡尔对自然的纯机械描述摧毁了自然世界目的论,又仍然发现了笛卡尔哲学的不彻底性。笛卡尔仍然肯定灵魂实体及其自由意志,保留了神对自然的超越性。
其后,吴增定老师呈现了斯宾诺莎的哲学前提——因果性原则或充足理由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原因,同时原因的实在性不小于结果的实在性。这一原则的革命性在于,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归结为一个动力因,其余原因尤其是目的因都是谬误。这是斯宾诺莎对经院哲学的釜底抽薪。此外,他强调了因果同质性原则,只有同类事物之间才有因果性。由此,笛卡尔的身心相互作用就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否定了目的因。目的因意味着最后出现的结果(目的)大于或等于原因,这是荒谬的倒因为果。
通过因果性原则,斯宾诺莎构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首先是实体、属性和样态所呈现的两个基本层次。这是说,实体包含无限属性,它自身是一个无限因果序列,体现实体的本质;而样态是属性的不同层次的具体表现,这里有直接无限、间接无限和有限的样态。这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内在性原则。在斯宾诺莎看来,神、自然和实体是一个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因果系统,后者不再有其他外在原因,以自身为原则,是自因,也是严格意义的自由。其次,斯宾诺莎基于因果原则批评了传统启示宗教和哲学。第一,他否定了创世说和神对自然的超越性,并认为神即自然,是唯一的实体。第二,他否定了目的论,目的是人的思想样态,作为结果不可能大于原因,并且和神、自然以及实体无关。第三,他否定了自由意志,作为有限思想样态,意志以其他样态和实体为原因,不可能是自由的。
除过理性主义的一面,斯宾诺莎也强调了力量和自我保存(conatus)。首先,他认为,神、自然或实体不仅是自因,而且是无限力量,由此提出了自己的本体论证明。神是无限力量,因此他必定存在,存在就意味着有力量存在。斯宾诺莎在此将神、实体转化成了无限的力量。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有限事物来说,情况则不同。他们的本质没有包含存在,因此具有自我保存(conatus),他们全力追求力量以维持自身存在。这也体现了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不同,霍布斯把自然权力只归于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斯宾诺莎认为conatus不只适用于人,而是体现在作为有限样态的万物中。人和万物在自我保存上是没有区别的,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人和万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能够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自我保存。其他事物只是通过本能方才如此。斯宾诺莎还将自我保存分为主动和被动的。前者是激情(passion),它基于错误想象,是一种不自由;后者是主动情感(action),它基于对自身和外物之因果关系的正确认识,是理性、主动和自由,体现真正的快乐。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的理性认识不仅是真正的快乐和自由,而且是对神的理智之爱,这也是神对人与自身的理智之爱。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这体现了斯宾诺莎身上的传统哲学残余。
在斯宾诺莎哲学的自我保存原则与因果性原则之间,显然充满张力。自我保存原则体现了他的思想中彻底自然主义的一面,反对任何形式的目的论,人没有相对万物的优越性;而因果性原则体现了他思想中的理性主义。斯宾诺莎认为,自然世界有内在必然的因果法则,这可以被人的理解所认识。换言之,人凭理解超越自然万物,实现自由。
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这一张力或者说不协调之处被尼采清楚捕捉。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吴增定老师谈到了尼采对斯宾诺莎的批评与改造。他清晰呈现了尼采在什么意义上肯定、在什么意义上批评斯宾诺莎。
首先是自我保存(conatus)与权力意志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尼采认为斯宾诺莎正确认识到了所有知识都是欲求(conatus),但他对conatus的理解是错误的。尼采与斯宾诺莎的区别是自我保存和权力意志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斯宾诺莎思想中有潜在的目的论,即把保存自身作为目的,这受到尼采的批评。尼采认为,斯宾诺莎把力量和欲求理解为两个东西,因为没有力量,方才欲求力量,在此,力量是客观外在的。而实际上,力量与欲求相同。尼采更愿意使用权力意志的说法来表明二者的一致。生命并非追求力量,而是本身就作为力量的释放和展开。自我保存是这种权力意志的退化形态,是生命的颓废。继而,尼采认为这种力量的释放不会停留于既定的、现成的状态,而是会尽可能超出自身,它是自我克服。人的整个个体与微观细胞均体现了权力意志的力量释放。世界有无限多的权力意志,它永恒地变化与生成,既没有神圣开端,也没有永恒目的,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掷骰子游戏”。
基于这种分歧,尼采对斯宾诺莎展开尖刻批评。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认为保存自己是失败的标志,是对真正生命本能的局限。对维持自身的设定是生命的颓废。在后期笔记与《善恶的彼岸》中,尼采的批评更加尖锐。他认为,自我保存学说是危险的,“要警惕多余的目的论原则”。作为自我保存的目的论体现了斯宾诺莎的前后不一致。我们可以通过尼采对斯宾诺莎的批评而追溯到尼采自己的思想。通过批评自我保存,强调权力意志,尼采将世界归为“力的怪物”。世界是各种游戏,由此,尼采走向永恒轮回学说。吴增定老师认为,尼采的形象与海德格尔理解的不同,他并不属于形而上学传统,而是这个传统的颠覆者。
尼采的斯宾诺莎批评所解构的是斯宾诺莎哲学中最核心的因果性原则。他使用谱系学方法对实体、原因和因果性原则的起源进行剖析,发现它们最终都源自人对变化无常、无秩序的力量游戏的恐惧和怨恨。为了消除自身恐惧与怨恨,人在无意识中简化和伪造了世界。对尼采而言,知识是人对世界的伪造而非发现。实体、原因、理性和因果法则都是人简化和伪造世界的工具,是“人性、太人性的”发明。尼采尤其批评了斯宾诺莎的自因概念,认为自因是“对逻辑的强暴”。他通过区分“说明”和“描述”概念而澄清了这点。尼采认为,描述是人的主观想象,科学是以因果为工具对事物的人化。事实上,并不存在原因与结果的二分,而只有连续的力量之流。原因和结果孤立提取了无限的连续流中的两点。
尼采的这一因果解释与休谟相似。所谓因果只是人的发明。人们认为事件总由主体发动,于是区分主体和行为。在尼采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人不仅误解了自己,还将这一原则推广至整个世界,认为动物、其他生命也有意图,因此,人总是询问“为什么”这个关涉目的因的问题。实际上,所有原因都是人对主体的虚构。这里的深层动机在于人对陌生事物的不安。人总要寻觅可遵循的、熟悉的事物来让自己安心。发现原因则使人不再恐惧。因果原则的发明是为了更好地自我保存。尼采把意志感、自由感也概括为原因,原因是动力也是目的。吴增定老师认为,尼采对因果性原则的看法是对休谟、康德和叔本华的因果理论的推进。与此相反,斯宾诺莎仍然认为因果性原则是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这是二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此后,吴增定老师提出,在尼采那里,哲学并非对神的理智之爱,而是对命运的爱。斯宾诺莎对传统的批评不够彻底,留下了神的阴影。他只是把神替换成可认识的因果必然系统。尼采径直认为上帝已死。要摆脱其阴影,就要看到世界是无限的权力意志,无限的生成毁灭。一切皆为偶然与机遇。由此,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之爱,所爱者即为理性必然系统。在尼采那里,生命作为权力意志对自身的无限肯定或爱,所爱者为偶然、变化无常、一次性和终有一死的命运。甚至无限意欲它再来一次,意欲自己的永恒轮回。这体现了二人对必然性的两种不同理解。斯宾诺莎的必然性是理性、自然和因果的必然性,而尼采的必然性是偶然的必然性。必然是对偶然的高度肯定。对命运的爱直接关涉尼采后期的重要思想永恒轮回。吴增定老师也提及了德勒兹对偶然性的看法与帕斯卡尔赌注间的关联。德勒兹认为,在赌注之下,帕斯卡尔对偶然的看法基于概率统计中的最大可能性。由此,偶然成为可计算的必然,仍然从属于因果必然性。斯宾诺莎对偶然的理解也是如此,他认为偶然仅仅源自于我们认识能力的不足。
这是尼采与斯宾诺莎针锋相对之处。斯宾诺莎认为,要肯定世界,因为世界符合理性秩序;尼采认为,要肯定世界,因为世界没有秩序,基于偶然。这一无原因的肯定是真正的肯定。
在讲座的结论部分,吴增定老师总结了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首先是斯宾诺莎对传统宗教哲学批判开启的两种解释可能:德国唯心论的理性主义解释与法国哲学强调的自然主义解释。这两种解释构成今天斯宾诺莎解释的两个主要方面,但它们都并不客观。其次,吴增定老师提出了尼采的斯宾诺莎解释与以上两种解释路径的不同。尼采看到了斯宾诺莎哲学中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双重形象。他很可能是通过二手阅读的方式最准确地理解了斯宾诺莎哲学。
在提问与互动环节,朱刚教授、谢裕伟老师、杨玉昌老师以及在场的听众与同学们,从各个角度向吴增定老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吴增定老师一一回应了老师同学们的提问。这场精彩、细致、深入的讲座至此结束。